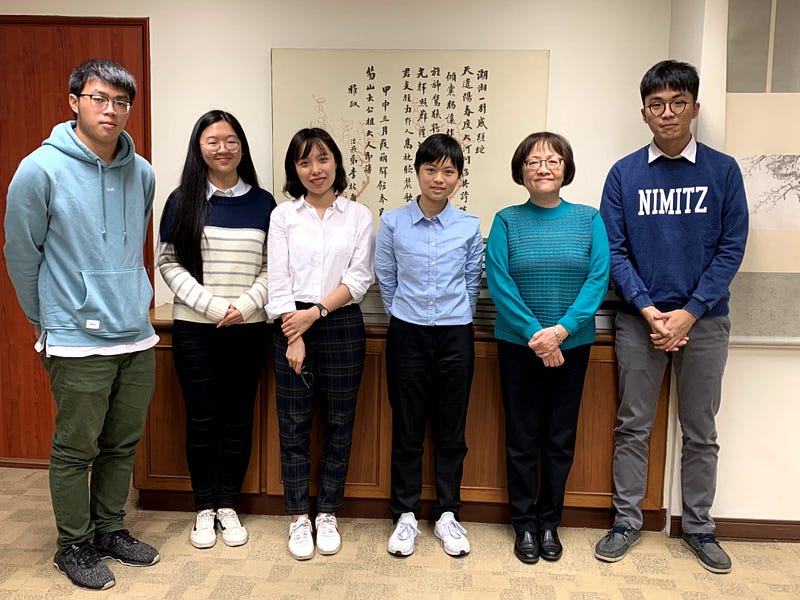▌訪談人:黃子晏、童冠傑、林婕琳、吳念恩、廖品硯。
▌撰稿人:黃子晏。
▌訪談時間:2020.1.16
▌責任編輯:柯采元
▌受訪者簡介:
呂妙芬老師,清大物理系、臺大中文系學士,臺大中文所碩士,UCLA歷史所博士。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暨所長。研究領域為明清學術思想史,特別是理學相關議題。

在一個陰冷的平日下午,我們來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研究所。走進呂妙芬所長的辦公室,溫熱的茶水早已沏好,與忙碌而特意撥冗的老師一樣熱情招呼著我們。
從物理學到理學
老師大學就讀清大物理系,畢業後又插班考進台大中文系,並繼續攻讀中文所,最後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。於是我們首先好奇,在曲折求學選擇中老師的心路歷程。
老師分享道,最初是對數學、物理感興趣,又因中學的歷史教育失於背誦與考試導向,因此考進清大物理系。大學階段,老師在追索生命的意義時,做了重要決定──成為基督徒,並於閱讀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歷史文化時,動念深入了解自身的文化根源。另一方面,當時清大剛成立中語系,從台大邀請了一些年輕教授來兼課,老師形容這些中文系的課是「艱澀理工課程中的調劑」,非常享受遨遊於教授講授的優美文學境界。物理系畢業後,老師不確定自己想做什麼,於是說服家人,插班考入台大中文系,繼續追求自己喜愛的古典文化。
碩士論文研究胡居仁與陳獻章。有趣的是,老師大學時從未接觸過宋明理學,過去閱讀思想史大家的著述時,甚至一直無法「進入」牟宗三先生的著作。不過老師認為,
理學之於中國的影響力,與基督教之於西方彷彿,「儒學作為從宋以來的官學,成為當時文化的基底,要研究明清社會的各個面向,很難避免這個基本條件」;
且文人優游於佛、道各教後,終於決定以儒學作為立命根本,有點類似皈依宗教的過程,理學家這般人生經驗吸引了老師。加以當時思想史研究正值高峰,因此老師想,「若只讀到碩班,不如做理學研究?」於是自己找了題目說服古清美老師指導。老師也順道提醒,自己找研究題目雖然困難,卻是很棒的經驗,對於題目帶有深刻情感不僅有助於研究,也有機會與老師對話,豐富研究內涵。
我們追問老師,從物理轉向中文所、歷史所,難道不會擔心畢業的出路嗎?老師說,1980年代的台灣經濟氛圍很好,物理系同學有些出國深造、有些則進入剛成立的新竹科技園區;即便是中文系,亦有廣告公司、雜誌社編輯、報社記者、廣播主持人等各型各色出路,因而當時沒有太擔心就業的問題。「本來寫完就不想再回去讀自己的碩論了」,老師笑道。因隨丈夫留美,才覺得有機會可以繼續研究。於是一面陪伴家人,一面準備考試,進入UCLA,向研究明清教育、思想史的歷史系教授艾爾曼(Benjamin A. Elman)學習,也是因此轉讀歷史所。
過去在中文系、所的學習,培養了一字一句紮實閱讀原典的剖析能力;歷史學的訓練則著重對脈絡與時序的理解,兩者共同培養了老師寬廣的研究視野。老師說1995–1997年開始重刊四庫存目叢書前,許多晚明史料都散在各善本書庫,因此她1992年進入博士班時,陽明後學研究尚未興起。自己的博論原先想做王畿與羅洪先的比較,因為羅洪先與王畿的關係從密到疏,最終兩人學術主張有明顯差異,分別代表浙中和江右學派,過程相當值得玩味。當初構想這個題目也類似碩士論文的選題,藉由比較兩位重要學者的思想與成學經驗來理解學術史的變化(老師的碩論研究胡居仁與陳獻章,探討從程朱理學至陽明心學的變化)。後來老師在艾爾曼教授的指導下,加入社會史的角度,以陽明學講會的研究完成了博士論文。

抓緊材料,看見新世界
進入近史所後,老師開始探討婦女及家庭、《孝經》、教育與宗教會遇等多元的素材,但認為自己「一直做廣義上的宋明理學的領域」。老師就讀UCLA時,婦女研究的意識逐漸揚起,每門課幾乎都會有討論婦女的專題,博論口考時,也有許多教授詢問老師,「講會中都沒有女性嗎?」老師指出,講會中確實沒有女性參與,但理學家的文集中卻有許多家中婦女如母親、妻子的墓誌銘,可以探討明代女性的生命故事。藉著近史所要開婦女史大型會議的機會,老師扣著理學的脈絡,提出問題意識:
「如果心性之學是成聖成賢之學,明代理學是個人道德與生命意義的追求,那女性有可能嗎?可能變成一位女性理學家嗎?」
老師表示,一般而言不太可能,當時女性較常做為虔誠的佛教徒;即使是對於觀念較開放的王畿,大概也覺得女人不可能學理學。不過老師饒富興味地說道,後來研究清初四川理學家楊甲仁時,原先打算從過去探討關中、河南的地域儒學,擴展到四川、福建;雖因資料零散而未能做成,卻意外發現楊甲仁曾與妾討論,對方與宇宙大化合而為一的悟道經驗,並從此與其妾成為「道友」。
至於《孝經》的研究,則是因為讀到羅汝芳弟子楊起元文集中,一篇儀式性的文本〈誦孝經觀〉,以及日本陽明學者中江藤樹文集中相當類似的文章,故動念挑戰「因為日本本土神道傳統,讓陽明學到日本帶有宗教性,而中國本土沒有」的觀點。
希望論證在晚明中國的陽明學本身也有宗教性。由於在日本「《孝經》和陽明學的關係眾所周知」,老師也想問:「《孝經》在中國,是不是一樣與陽明學有緊密的關係?」
查詢之下,老師發覺明代對《孝經》的討論相當豐碩,且確實與陽明學相關,於是開啟了漫長的相關研究,探討宋明理學與《孝經》的關係。做完前述研究後,事隔多年,陽明後學已變成研究熱點,老師於是選擇繼續以宋明理學為主軸,觀察明末清初理學變化,這一艱難富挑戰性的研究主題。
老師分享道,原先想研究晚明《孝經》的多元文本性質,但材料卻告訴自己不能停在晚明,因為晚明很多訴求要到清代才實現。儘管進入自己陌生的時代壓力很大,可是研究沒有辦法找到合理停止的地方。
「研究就是這樣,有時候它會帶你到一個很陌生、不舒服的景況下;可是它也會開啟你一個原先不太敢挑戰的新議題。」
老師謙虛地形容自己膽小的抓著《孝經》當繩索,緊抓著不放手,以免掉進茫茫大海而失去方向。雖然「研究不會是我想要怎樣,我最後都會走到,」猜了一個東西就開始去做,有時猜錯線索就斷了;但「有時候我看到新的材料,材料就會帶領我到另外一個議題。」談起過去想研究四川地域儒學,無心栽柳,卻轉而探討楊甲仁對女性求道的想法;或是雖難以發掘河南講會與《孝經》的關係,但發現清初河南有許多程朱派理學家及書院,正是呂維祺的下一個世代。老師眼中閃著熱情說道,
「材料會帶領我們走到另外一個、不一樣的世界。」

共同培養下一代的責任
聽完一位思想史學者的養成,接下來,我們好奇地請教老師任職所長的心得與展望。老師認為,近史所是個很特別的機構,聚集了約三十位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學家,約略與各大學相關領域的老師人數加總相等。近史所早期主要探討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,這幾年則對於「何謂現代性」有更深刻的反思。近史所同仁主要研究的時段是從晚明到當代,雖以中國史為主,但因近現代的中國快速進入世界體系中,且受到近年全球史風行的影響,目前許多老師都投入中西交流史、東亞史、全球史的範疇,「這些是跟世界各國共享的議題。」
老師希望近史所內豐富的資源除了能提供研究社群開展新的議題,刺激討論與研究外,也樂於辦理許多對外開放的學術活動。「在某個程度上,我一直很希望近史所的一些學術資源是可以跟台灣的高教共享的!」老師鄭重地說,
「我覺得年輕人的培養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的責任,臺灣有一群老師,可以共同來培養台灣下一輩的年輕學者。」
老師認為以漢學而言,臺灣的學術社群與資源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。在臺北能接觸到的講座、史料、師資比許多國外更好,研究視角已然和世界同步,知識疆界阻隔的問題也改善很多。但為什麼臺灣有這麼好的老師與資源,學生的碩士論文也普遍寫的很好,卻在求職的關鍵──博士論文,未必有相應的優秀成果?老師指出,一方面可能是因臺灣的獎學金太少,使得博士生需撥出許多時間打工而無法專注;另一方面,外國研究生課業壓力很重,需要全心全力準備課業,對語言不熟悉的留學生尤然,這種氛圍好像無法在臺灣見到。此外,台灣碩班、博班的課程沒有太大區別,而美國不同大學對於研究生的要求不同,一般對於博士生在修課上有相當的要求,而且好的學校課程選擇性很豐富。以上可能皆是影響台灣博士生表現的因素,但最主要可能是心態問題,如果系上的博士生每個人都覺得可以慢慢唸,就很難有人可以在五年內畢業了。
老師誠懇地說,「這件事讓我有點難過,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改變的話,我們很樂意!」因此,近史所內除了舉辦相當多公開演講外,所內老師們也到不同學校兼課,並讓研究生到所裡與研究員對談。近史所的老師們有感於臺灣研究生對於近代史領域興趣較薄弱,且對專攻的領域可能太早分工,近年來每年都舉辦研習營,希望提供研究生與大學高年級學生更多學習的機會。

給學生的建議
於訪談的後半,我們請老師對年輕學子分享一些建議與想法。問及老師認為怎麼樣的學生適合讀歷史系時,老師溫暖地笑道,「像你們很喜歡歷史的人就適合讀呀!」老師認為歷史是門寬廣的學問,大眾史學書籍與歷史劇中充滿人的生命故事,因而適合各年齡層的人。「要不要做專業史家是另一個選擇,但是我覺得人人都可以做歷史。專業的歷史學家其實是很窄的行業,但公眾史學的讀者群更多,這也可以列入考慮。」
談到對於喜歡歷史的高中生與歷史系學生的建議,「隨便~大學生就自由一點!」老師輕鬆地說道,並分享三種值得接觸的敘事手法:首先是閱讀,多讀小說對將來寫作有很大的幫助;而電影做為高成本的產業,鏡頭的拍攝、故事的敘述方法,每個環節都經精心設計,值得玩味;最後,去修習人類學系等不同學門的課程也很好,可以觀察人類學做訪談、田野的整體觀描寫。老師建議,「在大學時代,不需要想像自己的路是直直一條,因為你還很年輕、年輕就是本錢,有機會就多接觸一些不一樣的東西。」
而對於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學生,老師笑道,「職缺相關的東西不用想太多」。大學時若寫學期報告感到順暢,對這個領域真的很有興趣,不妨繼續讀碩士;碩士階段則是讓我們嘗試做原創研究的感覺,若過程仍很感興趣,就可以認真考慮讀博士。老師說,很多學生在寫碩士論文時便會發覺卡住了,此時可以回頭想想,「世界這麼大,我需要這樣嗎?喜歡歷史也可以閱讀史書,有需要刻意在浩瀚的文本世界裡找沒人做過的題目嗎?」老師認真地說,「如果不太確定,去上班也很好,在社會上可以學的東西很多,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也很多;反而專業的歷史學家,有時覺得做這些研究好像也沒什麼意義。」
「如果真的很有興趣,那就往前走!人就是要為了自己的興趣而活,做研究需要一點熱情。把資料累積到一定程度,撰文之後被一級期刊接受,沒有這麼難,可是要一直對於研究有熱情其實蠻難的。」
老師神情奕奕地分享道,偶爾對某些題目很有熱情時,醒來第一件事、睡前最後一件事都是在想它,思考如何連貫材料以敘述。如果真的對學術這麼有興趣、很想嘗試,即使同學可能已經賺大錢、買房子,自己仍甘於長年求學與物質不豐的生活,確定這就是自己想要的,「若是這樣,你就不要太擔心,總是會有工作的!」
老師也建議道,若想在大學時為研究之路累積資本的話,首要是廣泛的閱讀,「不用擔心自己讀不進去,讀多了就會有自己的經驗與想法!」若是可能,「趁年輕多學幾種外文,以後能做的題目會寬廣很多,這大概是我們這一輩老師最常鼓勵學生的。」此外,多接觸人文社會領域,例如修習人類系、社會系、中文系甚至外文系等課程,也很有幫助。行有餘力應該多多參加學術活動,開拓自己的視野。歷史學的範圍很廣,大學時慢慢摸索自己有興趣的主要領域,再進一步接觸相關的專業,如金融、貨幣之於經濟史,科學之於科技史,或是藝術知識之於藝術史等。
最後,我們請求老師給予一些面對挫折的建議。老師認為心態最重要,可以告訴自己「在挫折裡才能突破,如果一直待在很舒服的環境,不太可能有很大的進步。」如就讀UCLA時,面對陌生的歷史學,且是外文的環境,總覺得自己無法進入狀況,不過轉念一想,在這邊所學都是之前不熟悉的,代表學到的東西很多;用別人的語言來學,對自己而言都是進步與學習。老師溫暖地笑道,
「人生不同階段都會遇到不同的挫折,重要的是換個角度思考,讓事情出現正面的意義。大概人生就是這樣吧,當有事情過不去,我就會想,總不可能這件事情沒有任何正面意義吧。想到一個正面意義後,就緊緊抓住。」
從物理系到中文系再到歷史所,從宋明理學到婦女史、《孝經》與明末清初研究。在廣闊無垠的學海與人生汪洋中,老師總是緊緊抓住自己滿懷熱情的史料,緊緊抓住事情的正面意義,然後堅定地走向未知的前方。不知不覺間,老師與自己的研究,其實也為後輩開拓了一條溫暖而寬闊的道路。走出近史所,我們似乎也各自抓住了什麼,於是能更加勇敢的走向一個不一樣的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