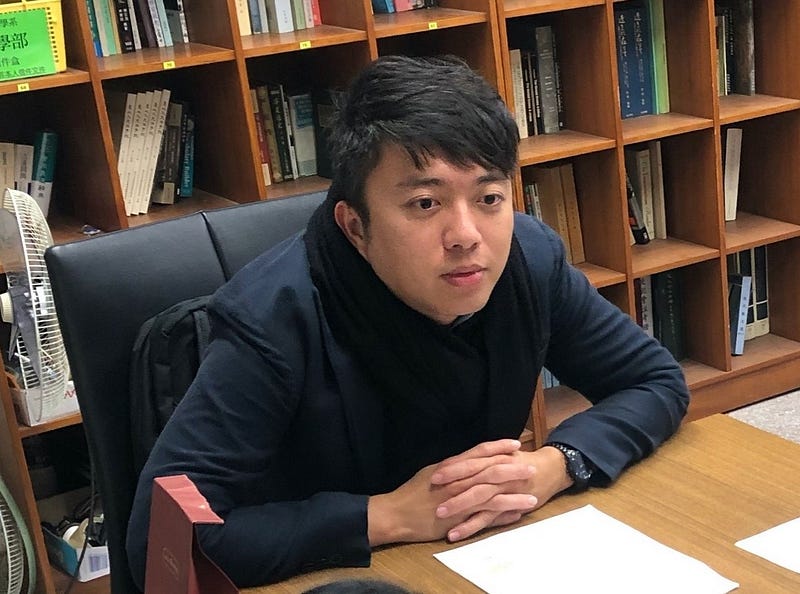童星的磨練:早熟與練達
嚴寒的聖誕節夜晚,訪問團隊與蘇致亨相約在溫暖的餐館,聆聽他與臺語電影、臺灣電影之間的故事。令人驚訝的是,原來蘇致亨早在年幼時,就與臺灣影視產業結下一段頗為深厚的因緣——他曾經是名童星!在意外地於信義威秀被星探挖掘後,蘇致亨小小年紀便開始面對鏡頭。起初拍攝的作品以廣告居多,待到有經紀公司挖腳後,他陸續出演如《戲說臺灣》、《流氓教授》等電視劇,更差一點接下《魔法阿嬤》主角豆豆的配音工作。
「背臺詞、演戲我倒是都辦得到……」被問起自己如何看待童星的工作,蘇致亨開始回憶,「只是我實在很難哭出來」。在大眾的想像裡,童星最能挑動觀眾情緒的形象,無非是劇中受了委屈、捉弄後,淚眼汪汪的可憐神情;為了捕捉童星們的苦瓜臉,劇組總得想方設法煽動他們的淚腺:威脅、嚇唬或是將他們的家人調離現場,種種方法只為換得童星們「淚」顏常開。但是這些招式,對小小蘇致亨一點都不管用,「我算是蠻早熟的,我就是知道他們在幹嘛、想要幹嘛,所以我就是不會哭。」就像是幼稚園就發現聖誕老人是父母假扮的一樣,早慧的他總是對劇組的「陰謀」見招拆招,讓劇組頭痛至極。
如此聰穎過人的腦筋,更讓蘇致亨在擔當童星、於演藝圈打滾時,便能夠對自身所處的環境做出敏銳觀察,進而反思自我。譬如他提及,即便每位童星都還只是小鬼頭,但小時候的自己便認知到,在童星圈裡大咖童星與一般童星間截然不同的待遇,儼然是階級化的具現。除此之外,蘇致亨在很小的年紀便明白,自己的性向與屬於主流的異性戀有些歧異,他遂有意識地表現得像是名異性戀男性,刻意掩藏自己的性向認同。如此行為也讓蘇致亨嘆道:「我算是摸透了一種『遊戲規則』吧!」
升學的歷程:理解遊戲規則
前段所說的「摸透遊戲規則」,雖然看似是蘇致亨回顧幼時人生的感嘆,「但其實每件事情運作起來,背後都有一套規則……」他說道,「一旦掌握它,解決起來就會簡單許多。」今日的蘇致亨雖能夠信心滿滿地談論他通透的各種遊戲規則,但要培養起這樣的理解力並有所轉換、運用,絕非一蹴可幾,於是他便娓娓道來自己升學路途的「絕地大反攻」。
在高一下學期時,對人文、社科等學科富有廣泛興趣的蘇致亨,聽聞「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」招生的消息後,便興起報名參加的念頭。報名人社營須附上備審資料供教授審核,通過後還需要進行二階面試,儼然是申請入學的翻版。蘇致亨順利通過初試後,從台北前往台中進行面試,怎知這一趟卻成了他終生難忘的挫敗經驗。「談談你有什麼喜歡的書籍?」面對如此經典的問題,蘇致亨不急不徐地說出《如何閱讀一本書》並簡介起來。「很好。還有呢?」沒想到面試官的追問卻震懾了他。他左思右想,情急之下什麼書都想不到,最後只得給出「國文課本」這個答案,「我那時就真的覺得國文課本不錯看嘛……」他笑著辯解道。而也正因為這樣的面試表現,最後他沒能如願一償參加人社營的願望。
在經歷人社營面試的慘痛教訓後,蘇致亨他反省起面試時的挫折,想想在那樣的場合,面試官、教授們會希望聽到他給出什麼樣的答案及反思,自己又應該做足哪些方面的準備。從那之後他繼續探索自己對人文及社科學科的志趣,閱讀書報、追蹤時事,培養對人與其組成的社會有更深刻的理解。其中,蘇致亨強調「台大社會營」是他在高中階段的關鍵啟蒙經驗。當時他讀到吳嘉苓老師所撰,討論台灣助產士興衰的文章,[1]令他訝異的是,原來台灣擁有世界第一高的剖腹產率,以及這樣的數字背後,潛藏國家、技術、科學的力量於其中拉鋸,也讓蘇致亨驚嘆:「原來日常生活中、社會裡頭、台灣島上能有這樣的事情!」進一步增進自己對於觀察宏觀圖像與細瑣現象鍵結的聯想力。
經過幾番磨練,蘇致亨最後胸有成竹地逐步定立志向,取得學校的推甄名額報考臺大社會系。他縝密地搜尋好社會系各老師的資歷、文章、擅長領域等,並閱讀社會系面試「寶典」:《社會學動動腦》、《見樹又見林》,可謂做足全面的準備,令他能夠抵達面試場合,一一解決老師們的提問,令他們大為驚嘆。蘇致亨依循「遊戲規則」的表現,遂成功獲取臺大社會系的門票,一雪人社營面試失敗的前恥。
進入臺大後,蘇致亨也依循著各堂課的「遊戲規則」理路,遊刃有餘地應對大學課業。在當大一新鮮人時,他修習社會系的必修課,該門課雖然直至今日都不是一門給分甜、要求涼的爽課,但蘇致亨就是能夠掌握該門課的「規則」,輕鬆地背誦、理解重點,俐落地在一次次的作業及考試中取得高分。既然已經領會修習硬課拿高分的要訣,那麼修習難易適中的課程,自然難不倒他,他遂在入學就拿到「書卷獎」殊榮。講到這裡,蘇致亨不禁脫口而出:「我就會不喜歡那些『人社(營)帝國』的人阿……我就是那個你們當年不錄取的人,現在我卻拿到書卷獎!哈哈!」他俏皮地為自己錯過人社營,卻靠著機智與努力異軍突起的歷程,下了令人會心一笑的註解。
研究的志向:說出想說的話
回憶完自己的求學經歷,蘇致亨開始道來自己如何從單純的學生,決定步上研究者的道路。令人驚異的是,學術研究一途,蘇致亨起初是不看在眼裡的。這就要說到他高三時參與社會學年會的經驗,該會為一年一度聚集眾多社會學學者、研究者發表研究的場合,並開放高中生、大學生免費參與。蘇致亨憶及,自己聽了兩天下來只感到「非常無聊」,在17、18歲的他眼中,這些研究都是專注在「OOO為何會成功?」、「XX現象何以能夠生成」,此類「跟在別人成功屁股後面」的成果,沒有值得向外人道之的創見,這讓「學術研究」一詞,在年少的他心中留下稍嫌負面的印象。
因此蘇致亨進入社會系後,起先決定按著自己的興趣讀書、修課,但他也有了在課堂、教室外進行探索的契機。在他大二的時候,受到學長邀約參加異議性社團「濁水溪社」。原本蘇致亨同時段已經選修一門課,但實際修起課後,有些不合他的胃口,遂答應學長的邀請參加「濁水溪社」。他回憶濁社的社課都在認真地做讀書會,觀賞與臺灣相關的各式書籍、影視作品,因而大量接觸台灣史、台灣電影、台灣文化,不僅讓蘇致亨補了一門「台灣史」的課,更從中對其產生興趣,豐富了自己的視野。
但另一方面,儘管擁有多樣的大學經歷,蘇致亨對於學術研究的觀念,卻不知不覺地隨著他在大學的探索而有所轉變。蘇致亨在大學時,幾乎秉持著「非紮實課不修」的理念,在社會、戲劇、外文等系的「魔王課」來回遊蕩。儘管過程辛苦,卻也磨練出一套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模式。譬如社會系劉華真老師、林國明老師的比較研究、政治社會學課,學習從國家、制度層面,發展出宏觀而細緻的觀察視野;或是外文系沈曉茵老師的台灣電影課,透過鏡頭語言、劇情鋪陳等分析工具中,解讀經典台灣電影文本的另一番趣味。經過這些課程的洗鍊,「考取研究所」這條路也不再被蘇致亨拒斥在選項之外,他也漸漸對「學術研究」改觀。
大學四年過去,到了即將畢業時,蘇致亨為畢業後的兩條路做掙扎,一是延續自己在社會系外的探索,走戲劇、劇場工作;另外一條路,則是接受更嚴密的社會學學術訓練,繼續攻讀社會所。幾番考量後,蘇致亨做出了抉擇。「我不想要演別人的戲,喜歡自己當編導。」他說,「但那時卻又沒有什麼特別想說、想傳遞的話。」因為他所認為的「戲劇」,就是要透過表演來傳遞自己想說的話或是觀察的現象,既然如此自己應該先紮穩馬步,潛心去徹底瞭解、研究自己究竟想說的話、想說的現象是怎麼一回事,不讓戲劇的呈現顯得蜻蜓點水,流於表面。至此,蘇致亨對學術研究的本質有了不同的理解——「透徹地理解現象」,而非僅只是仿若誠品排行榜的「成功學」之流。因此他便決定待在訓練紮實的社會所。
考取研究所之後,困難的事還在後頭——尋找感興趣的碩士論文研究課題。儘管就著在「濁水溪社」培養起,對台灣、台灣史的廣泛興趣,加上童星經驗潛移默化的影響,「台灣電影」這個領域一直都吸引著蘇致亨。再加上大學後,他也持續接觸戲劇系、外文系所開設,與戲劇實作、影劇分析有關的課程。此外,2008年《海角七號》締下的成功,讓台灣電影再領風騷、影視產業蓬勃興起,使得「台灣電影」成為蘇致亨眼中的一時之選。但究竟要怎麼研究台灣電影、用什麼方法切入台灣電影,仍舊困擾著他。一開始,他考慮的是文本分析式的研究,但這樣的途徑卻與所內的主流大相逕庭,令他為之卻步。
隨後,蘇致亨先以「台語片為何在短時間內急速消失」為問題及大方向,開始搜索資料及證據。寫作碩論前期,他感到十分茫然,絲毫沒有頭緒該去挖掘哪些線索。但這個時候,因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》爭議而起的太陽花學運爆發了。本於對社會、公共議題的關注,蘇致亨亦投身其中,但他並沒有就此荒廢碩論的進度,反倒因為學運而有了頭緒。他從整體的電影產業作切入,將產業的運作釐清之後,發現作為生產關鍵原料的「底片」這項因子。「因為太陽花就是因貿易問題而起的,我就想到底片進口會不會是一項關鍵因素。」蘇致亨陳述自己找尋證據的經過,「結果到了關務署調資料,就有了驚人的發現。」原來,不生產電影底片的台灣素來仰賴美國柯達、日本富士等大廠的底片進口,但底片進口數目卻在台語片數量驟減的年代應聲跌落,讓他發現兩者的連結。
在那之後,蘇致亨逐步開展研究的理路,蒐集檔案資料、拼湊關務證據,以豐厚的史料證成台語片的消亡,與國民黨政府用不補助小額生產的黑白台語片、獎勵大成本製作的彩色國語片等等,「抑台語、揚國語」的黨國文化治理息息相關,他的作品更拿下多項傑出碩士論文獎項,成果斐然。
改寫成書:曾經,台灣有個好萊塢
雖然蘇致亨的碩士論文屢獲好評,但他想做的事遠遠不止於此。對他來說,投身台灣電影、台語片研究的目的,始終是「為沒有光環、沒有歷史的台語影人發聲」。於是,他又陷入了抉擇。蘇致亨這次的兩條路,一條是做現今流行的「知識普及」,也就是開設一個粉絲專頁或是YOUTUBE頻道,分享一些有關台語片的知識;另一條路則是改寫碩論成書,蒐集更多元、龐雜的資料與證據進行更縝密的研究,將台語影人的觀點納入作品,而非如碩論僅止於論證「台語片為何急速消失」。這次蘇致亨並沒有猶豫太久,毅然決然地選擇後者。
其實改寫成書的想法,在寫作碩論後期就潛藏在蘇致亨的心頭。之所以抱持這個想法,一來是因為在他之前,就有許多臺大社會所的學長姐改寫碩論成書,各個都得到不少好評,二來是因自己認為,從事普及工作總有不知該普及什麼的一天,倒不如紮實地研究並撰寫一部有影響力大部頭書籍,或許更能為台語片、台灣電影有所貢獻。
改寫工程十分浩大,除了在架構上必須加入台語電影發端的前身——日本時代電影發展之外,蘇致亨更得親自口訪一位位台語片導演、攝影師、演員等影人,有時因為問題設計得不好,導致老影人們一問三不知,光是採集寫作資料便煞費苦心。所幸改寫工作得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資金贊助,而且蘇致亨在畢業後更得到國家電影中心(今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)研究組的工作,在裏頭得到不少外面所沒有的檔案、史料。此外,蘇致亨更談及,那些受訪的老影人有時也不吝惜地傾囊相助,譬如藝名陽明的蔡揚名先生,便會仔細地閱讀蘇致亨的稿件,不時給予叮嚀、建議,令蘇致亨大為感動,且更能夠用當事者的視角描繪出1950、60年代,那台語片產業人聲鼎沸、蓬勃發展,有如「台灣有個好萊塢」的美好盛況。
經歷無數個白天工作、晚上趕稿的日夜,又因為死線、靈感不足、作息壓力暴食之下而體重激增,蘇致亨不減其自寫作碩論以來的嚴謹態度,最後經歷近五年時間,在2019年底他終於端出《毋甘願的電影史》這部圖文並茂、內容充實且可讀性高的作品。
談起《毋甘願》這本書,蘇致亨的寫作意圖又不只是希望讓大家知道台語片的昨日風華。「我們對文化的瞭解,其實一直是很菁英的。」蘇致亨說,「當我們將關注文化的視野,聚焦在菁英的文學、藝術時,就不會知道音樂、電影這些底層、庶民們的文化是怎麼回事。」原來,在蘇致亨心裡希望做到的,是更透徹地理解底層社會的模樣,知悉台灣大眾究竟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,對他來說,進行台語片興盛衰亡的研究,恰恰連結了庶民娛樂體驗與高層政治治理的關聯,讓作為研究者的自己及台灣大眾,能夠更深而廣地觸及吾人父祖輩台灣人的心靈。
接續著這樣的宏願,蘇致亨說:「我覺得我要繼續擔任「中央廚房」的角色」意即持續產出台灣電影史的文章,深化戰後台灣文化史研究,挖掘更多能被世人傳唱的台灣電影故事。未來,蘇致亨想深究台灣文化的整體轉型過程,將研究視角後推,推至以往碩士論文止步的1970年後之「蔣經國時代」。在今年春山出版之《看得見的記憶》一書中,已能見到蘇致亨以「新電影」的生成條件為題,作為《毋甘願》後的初試啼聲,且讓大眾繼續期待,關注他未來所要帶給台灣大眾的精采故事。
給高中生的話:好好地玩吧!
「給高中生的話嗎?我好像距離高中真的太久了……」蘇致亨歪起頭,左思右想著,「那應該是,要他們好好地玩吧!」他回憶起高中的生活,想起在高中時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人。高一時,沒有經過類組、志趣的分班前,大家混在同一班無忌地相處;抑或是待在社團,同樣沒有太多分類,一群背景差異甚大的人,為了一件有趣的事齊聚一堂,用力揮灑青春的汗水。他認為上大學之後,每個人就多半會和學習目標、休閒嗜好等處同質性較高的人聚在一起,就像自己上大學後大抵都在讀書、鑽研自己感興趣的課題,少有再廣泛地接觸背景、志趣完全不同的人。「好好地玩吧!」不只是如字面上好好地遊戲高中人生,更是旨在珍惜高中所擁有的殊異及多樣性。
[1] 讀者若對該文章有興趣,請參見吳嘉苓,〈醫療專業、性別與國家: 台灣助產士興衰的社會學分析〉,《台灣社會學研究》第四期(台北:2000),頁191-268。
受訪人簡介:
蘇致亨,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碩士,專事研究台灣電影史,尤以台語電影見長。曾任職於國家電影中心(現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)研究組、文化部。
其作品有:
-
- 《毋甘願的電影史》:本書以蘇致亨之碩論〈重寫臺語電影史:黑白底片、彩色技術轉型和黨國文化治理〉為骨幹,以鉅觀的產業史、文化史視角進行大幅度擴寫,重新梳理出臺語影人們從日本殖民時期發端,到戰後1950年代起大顯身手、影壇百花齊放,卻因物質、技術、政策等因素阻撓下,「毋甘願」地讓臺灣好萊塢止步的故事。
- 〈天才何以成群地來?臺灣新電影的生成條件〉:本文收錄於《看得見的記憶:二十二部電影裡的百年臺灣電影史》,以侯孝賢的《尼羅河女兒》為起頭,以整體性的產業視角,分析並指出1980年代「新電影」浪潮,在「資金」、「技術」、「獎項」三個因素作用下,新電影影人、創作得以迸發而出,創造台灣電影史重要的轉捩點。
訪問人:廖品硯、柯采元、謝孟吾、馬銘汝、劉暢、顏恩杰
撰稿人:廖品硯
訪問時間:2020/12/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