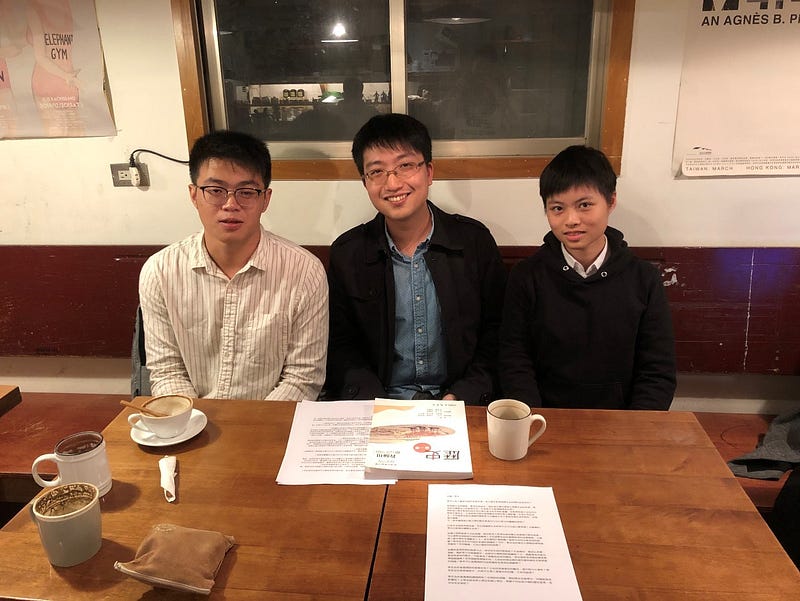從醫學系到歷史系
在一個冷冽的下午,溫暖的咖啡廳,我們與王紫讓學長進行訪談。首先,我們問到學長過去的科系選擇。學長表示自己當初進入醫學系的原因,是學測時考到滿級分,順勢而為進入醫學系,當時對自己沒什麼太大規劃。然而,進入醫學系意味著接下來的道路已被定性,將來數十年的生活,主要就是在醫院工作,不會有太大變化。如此環境不符合學長熱愛自由的性格,加上學長個性較喜愛獨來獨往,和重視內部緊密連結的醫學系也有些格格不入。因此,雖然覺得醫學很有趣、很好玩,但不是這麼想當醫生,終在大三時決定轉往歷史系。
談到轉系時的科系選擇,學長笑著回答:「歷史很有趣啊!」除了歷史學外,學長對於人類系、昆蟲系或森林系等一般較不被社會大眾看重的科系都相當有興趣。至於為何最後選擇歷史系?學長以昆蟲系為例,認為昆蟲系須要專精在較小的單一領域,之後的道路也相對被限定,如此一來似乎會重蹈過去醫學系的困境,難以學到其他感興趣的東西。所以後來學長才選擇了一個看似不專業,但實際上也相當有技術性,且必須大量閱讀,可以看到非常多資料的歷史系。
進入歷史系時,學長並非一開始就決定要往學術的方向走。最初會轉往歷史系,主要是覺得歷史很重要,抱著嘗試的心態,想來看看世界之大。學長提到,雖然歷史學一般來說不受社會大眾重視,但事實上絕對不是那麼的沒用,「不然為何每次要改歷史課綱時都會有人跳腳呢?」,歷史往往形塑著人們的記憶與認同,辨別一群人的過去是共享,抑或是疏離,因此學長認為歷史學是非常重要的。此外,學長認為歷史學雖與「說故事」不完全相同,但某方面其實相當類似,皆重視時間的演變與過去的重現。另一方面,現今歷史學也相當「科學化」、重視證據,論證過程和數學證明相當類似。在個人層面上,也能提供人們更寬廣的視野,讓生活變得更好。
國外求學經歷與對中東的關懷
再來,我們也相當好奇學長的國外學習經歷:學長曾因為對古代中東的興趣,抱著某種神秘的好奇,至伊朗德黑蘭大學學習波斯語;也曾申請教育部獎學金,到英國倫敦亞非學院修習亞述學。亞述學是研究古代美索不達米雅與鄰近文化的一個研究領域,由於亞述的考古發掘成果較早,所以就約定俗成的稱之為亞述學,並不單指亞述本身,亦包含鄰近的數個文化。學長提到,當初對亞述學感興趣的原因,是因為古美索不達米雅不僅孕育出首個複雜,且與異文化有較多接觸的文明,還擁有非常古老的書寫系統,這使得在歷史與文明研究上,美索不達米雅有其特殊、重要的地位。也正是這兩河文明的璀璨,牽引著他走進了亞述學的世界。
出國讀書的經歷,讓學長體驗到一些以往感受不到的事物。例如英國與臺灣的師生關係有很大不同:倫敦亞非學院相當重視師生間的交流,學生在下課後會和老師一起去pub相互聊天。在伊朗生活,也使得學長較能理解當地人住在什麼樣的環境、有著什麼樣的概念,進而對固有想法產生衝擊。比如說,不同於臺灣的生活和海密切相關,學長在伊朗時,發現自己身處廣大內陸的中心,離最近的海都有很長一段距離;伊朗德黑蘭的北邊是高山,但山上植物不多,所以當地人對植物的看法,與台灣有很大的差別:古代伊朗的木材是奢侈品,華麗的宮殿由許多昂貴的木頭所製成,和常見木製民房的台灣有顯著不同。實際了解當地情形,對於認識當地的歷史、社會都相當有幫助。如同馬克思所說,下層結構影響上層建築,下層的生產方式、經濟活動、社會結構等因素,都會決定著人們的心態與思考方式。因此,學長認為歷史學者研究過去人們的生活,所以他應該要是「生活行家」:也就是在自身生活中,擁有敏銳的感受、察覺能力,而這也是藉由讀歷史,所能培養出來的重要能力。
回首過往,學長提到他在亞非學院的那一年,學了幾種語言、寫了個研究計畫、並曾在研究生研討會中發表,也參加了巴黎的世界亞述學大會。雖然做了非常多事情,但學長反而認為當初花太多時間在研究學問本身,讓自己疲於奔命、不甚健康。因此,現在學長相當重視自由、快樂、健康,在訪談中也不斷提及這些概念。
自由、快樂、健康、大量閱讀,以及拋開功利心——對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建議
自由、快樂、健康、大量閱讀,以及拋開得失、功利心,是學長在整個訪談中數次強調的觀念。一如先前提到因為追求自由而離開醫學系,選擇歷史系,學長也建議高中生、以及初入大學的歷史系學生,生活作息不必太正常,重要的是讓自己覺得快樂、沒有受到壓迫的感覺。在生涯規劃方面也是如此,現今社會變動快速,計劃時常趕不上變化,盡量讓自己的規劃保有一定的彈性空間,並保持對世界的好奇。重要的是保持彈性、好奇與快樂,找到屬於自己的平靜。
另外,學長對於「旅遊」方面也是頗有心得。學長認為藉著旅行,可以看到當地風土與習慣,這些東西對於歷史學研究都是很寶貴的。因為古代生活與現在時常差距甚大,歷史學研究的又是過去人們的生活,所以想像、「模擬」過去人們生活樣態對於歷史學研究相當重要。那要如何獲得這些模擬的能力呢?學長認為用心生活、有更多生活經歷與大量閱讀,都是培養模擬能力的不二法門。再來,要了解一時一地的風情,必須掌握其「語言」。學長曾學過英文、法文、土耳其文、希伯來文、波斯語、蘇美語和阿卡德語等多種語言。學習這些語言的契機,主要是為了因應研究對象,例如在伊朗學習當地官方語言波斯語,或是為了閱讀舊約聖經而學習希伯來文。由於沒有抱持著太大的功利心,所以學習時也沒有感到太大挫折。但多少還是有遇到些困難,因為當中許多語言,都是不再有人以之作為母語的死語言。相較於現代語言,學習古代語言時媒介較少,更注重背誦,所以也非常容易忘記。不過學長認為,學習語言不必看待的太過認真、嚴肅,主要就是憑藉著興趣。總之,學長認為旅行無論在語言、「模擬能力」方面都是一種學習,歷史學也總是離不開生活。
「大量閱讀」是另一個學長在此次訪談中,不斷提及的概念。對歷史有興趣的高中生、大學生,無論日後是否決定走學術這條路,大量閱讀都相當重要。大量閱讀的原則為何呢?必須拋開功利心、保持興趣、廣泛的涉獵,不一定都要讀歷史學相關書籍,讀覺得好玩或是需要的東西就好。閱讀時,不須感到太大壓力,尤其在這個緊張焦慮的現代社會,能夠「自得其樂」相當重要。對大一、大二學生而言,此階段沒有到要產出論文的地步,所以也不必讀到太細,此時期的精讀,以能夠寫出一份好的摘要、期末報告為目標即可。此外,學長認為如上課指定閱讀等書目中的論證過程大致了解就好,重點應放在論文、書籍的結論。所以,假如沒有太多時間閱讀資料,那至少我們應該記住結論。倘若過了一段時間覺得結論有些怪怪的、不是那麼有說服力,再回來看它的論證。總之,學長認為透過廣泛閱讀,可以培養先前提到的「模擬」能力、找到自己喜歡的領域,以及找出重點,了解哪些資訊重要,哪些不重要的能力,非常鼓勵高中生與大學生多多閱讀。
訪談結束時,也近乎夕陽西下了。整場訪談下來,學長不斷提醒著我們應當時時保有自由、快樂、健康的心態,用心體會生活,並大量閱讀有興趣的書籍、文章。最重要的是,要保持著「自得其樂」的能力。

受訪者簡介:
王紫讓學長,現為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。原先就讀於臺大醫學系,後因志趣不和,在大三時毅然轉至歷史系。曾赴伊朗德黑蘭大學學習波斯語,也曾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修習亞述學。
訪談人:王安珩、曹希君、詹益寧、鍾承樾、曾聖軒、張凱傑
撰稿人:王安珩
訪談日期:2020/12/20